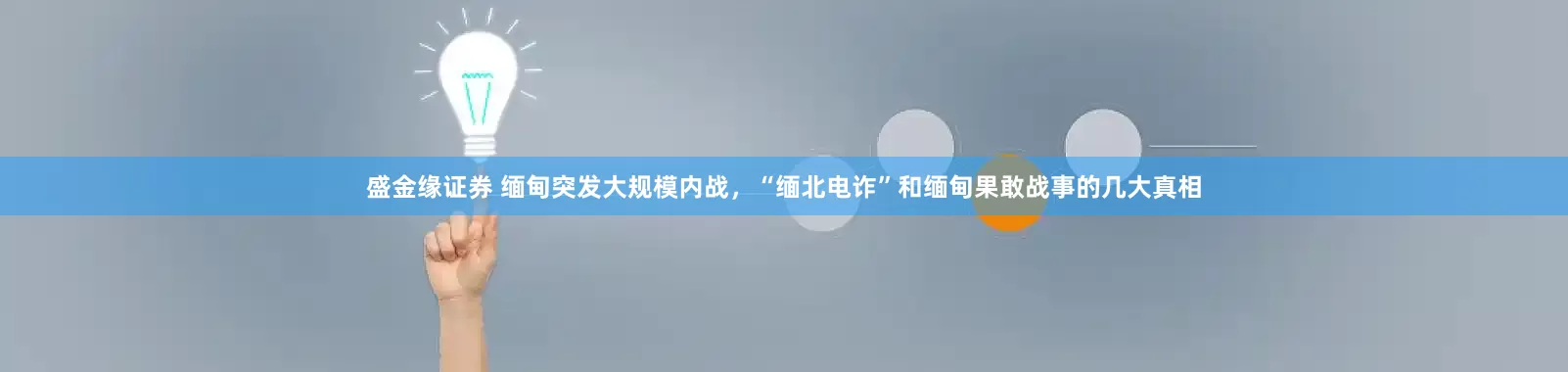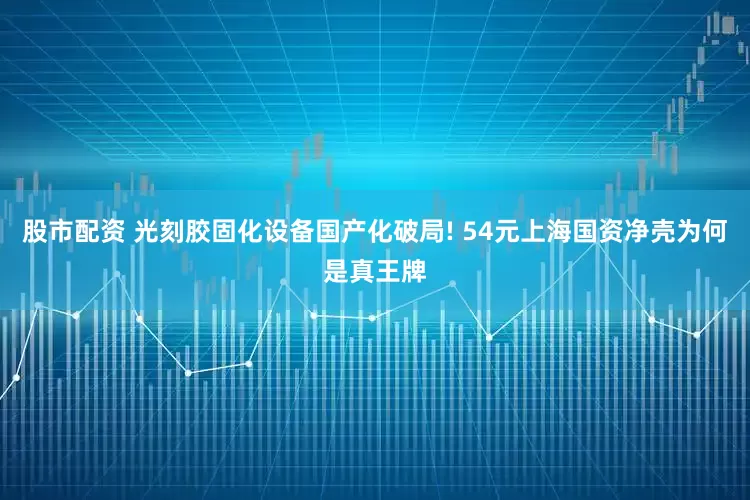尚融 唐均:“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中的东方主义羁绊和汉学主义突围

)Tatar“《阙特勤碑》东面第4行:三十姓鞑靼尚融,系指突厥东面、契丹之北的原蒙古语诸部”40;作为异体的Tartar,其拼写受到拉丁文Tartarus“(希腊神话)地狱”影响,源出希腊文Τάρταρος~Τάρτᾰρᾰ“深渊,泰坦幽禁处”。
在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国家和民族,既有近代以降一直居于世界文明高地的欧洲,也有曾经孕育出各自灿烂历史的亚洲和非洲。以中国为龙头的“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既要着意于整合多种民族意识和文明要素,更要让中华文明的优秀元素和丰富内涵为异族所认知和接受。

自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文明在全球的地位一直沦为欧美高高在上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视野审视之中:或为光怪陆离的猎奇式他者(xenophilic),或为与西方割裂的妖魔化异质(xenophobic)。
即便是中国已然成长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导世界话语权的欧美世界仍然难以摈弃其东方主义的中国视角,从而引发刻意针对中国的大量敌对行为,其目的之一就在于阻挠和破坏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文化建设。
因而,站在文化研究的比较立场之上,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如何从文明传播和交融的视阈,逐渐消解西方意识形态布下的东方主义羁绊。
然而回顾西方对中国的早期审视目光,我们发现并不一贯如是:
远的不论,从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历中国到18世纪末耶稣会士的退出中国,排除其中意淫般的想象成分,我们可以看到,严肃谨慎的西来者们更多是以一种汉学式的眼光,对中华文明的多个层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这笔意识形态的遗产在今天,更有值得整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必要。
近年来出现并有所争议的汉学主义(Sinologism)思潮,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可以视若我们扬弃东方主义理论藩篱的有力武器。
作为后现代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产物,汉学主义约产生于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最初释义为“汉学中的东方主义”1或“汉学研究的东方主义”2,其主要论点是汉学不是一门学问或知识系统,而是“想象”、“神话”和“意识形态”,所塑造的“文化他者”话语,不仅表述知识,而且显示权力,体现出汉学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之间的一种关系3。

事实上,这种观点的“汉学主义”主要是从汉学这个学科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确定的,实际上对汉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客观性也是根本怀疑的:在学科基本假设上,经典汉学已经把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死去的文明来对待;在学科体制上,汉学是归属于现代西方学科体制的,故而在东方学体制下,汉学研究不是接近中国而是疏远和排斥中国,这样,整个西方汉学史就证明汉学只是一种西方塑造文化他者的话语4。
然而,区别于根植近东研究而衍生的东方主义,汉学主义实际上是由西方构建并运用在西方与中国的接触时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事务和阐释纷纭复杂的中国文明的认识论进而演变为意识形态,反映的是西方学者和非西方世界在中西方接触时所持有的一系列观点、信仰、态度和价值的总和5。
其理论基础早已扬弃了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束缚,发展成为基于“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进行的考量6;相较于东方主义论及为殖民铺路的或隐或显观点、思想、信仰、意识形态和学术行为,汉学主义从根本上讲却是一种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认识论、方法论和西方视角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并因中国人和非西方人的参与,从而复杂化的、全球性的、多边构建的理论范式和文化现象,其中不仅有西方人通过西方视角对中国文明的观察,更有中国人通过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世界、对自己的文化,以及对于自身的观察7。

这也就是说,虽然历经短短20来年左右的发展时段,但汉学主义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历经了故步自封于传统东方主义麾下的沉静和停滞,已然飞跃到一种西方汉学体系与中国本土思维有效碰撞后达到的有机整合和能动叙事阶段,中华文化本有的吐故纳新能力,正在践踏出更加客观的审视、阐释远东独特文明的新路。
在今天多方鼓吹的“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浪潮中,固守东方主义的窠臼,无疑将会笼络住我们的意识,从而羁绊住我们的行为;而突破相沿成习的东方主义羁绊,新兴的汉学主义思潮,未尝不可小试牛刀。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元素集大成者的小说《红楼梦》,本是满汉文化融摄的产物,迄今已有150多种语言的不同篇幅译文(本)出现8,其中丰富的东方文化元素久经西方语言碰撞,自然可以作为东方主义和汉学主义一较高下的试金石,故而,《红楼梦》的多种译本在相当程度上也不啻考察“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可靠样本。
下面我们以《红楼梦》中仅出现一次但内涵纷扰、而在迻译时又歧见纷出的“骚达子”一词及其多种欧亚语言译文为例,看看译者们是如何自发消解东方主义的窠臼羁绊,又是如何自觉实现汉学主义的范式突围的。其间参考文献的引用,若未有特殊说明者,皆以其通行本为准,不赘。
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9:

一时湘云来了,穿着贾母给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子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妆出个小骚达子样儿来。”
首先我们注意到,在本文涉及的多种对应译文中,黑山斯洛伐克译文之Aspoň podľa toho, čo má na sebe oblečené10“至少从穿着上看如此”乃承前文之“孙行者”而进行的转述,符合其迻译《红楼梦》一以贯之的讲述特色,存而不论;而裘里之英译a young bewitching ape11“年轻的蛊魅猿猴”,在英译者自陈其“为了保存原作的含义,不甚注重音律”12(the text has been more adhered to than rhythm)13宗旨辉映下,不仅显得离题万里(但比解作“小骚羊羔儿”14恐怕还是要靠谱些),而且还笼罩着一种猎奇式的他者情调,正是彼时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臣民面对全世界的东方主义眼光之自然流露。
其次我们再来认真审视上述《红楼梦》原文,这里是根据程乙本而出的引文。虽然《红楼梦》版本纷繁,文中关键词句异写众多,但在这个细节之处却是高度一致的:俞平伯八十回校本15、三家评本16、程甲本17皆是如此;而在庚辰本18、戚序本19、蒙府本20、甲辰本21、梦稿本22等迄今可见的脂评本中亦复如是,概无分歧。

唯程甲本在整理出版时另有注释详述23:
小骚达子——又作「小臊鞑子」,本是一种侮称。骚:狐臭。《山海经·北山经》:「食之不骄。」晋郭璞注:「或作骚。骚,臭也。」同「臊」。臊:肉类及油脂的腥臭气。鞑:即鞑靼,蒙古族别称。宋彭大雅《黑鞑事略》:「黑鞑之国,号大蒙古。……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大银。」这里是一种戏语。
其实,这段注释可以视若此际中文世界的红学家对其内涵的权威认定。
从南北朝开始,“鞑靼”一词在汉籍中就有了纷繁芜杂的相关记载:大坛~坛坛(柔然)、达怛(室韦)、达靼(靺鞨)、塔坦(塔塔儿)、鞑靼~达打~达达(蒙古)等(将其视为波斯语“父亲”一词的转译、从元代开始才进入中国24则大谬不然),其指称范围随时代和民族不同而歧异较大,不一而足,但总的来讲都是对出现在欧亚大草原上不同游牧民族的泛称。从而,“鞑靼”一词先天具有沟通丝绸之路、振荡欧亚大陆两端主体民族的特质。
而自蒙元以来,从“鞑靼”一词衍生出来的“达子”“鞑子”“鞑虏”等,便成为汉人对北方以(原)蒙古人为主的游牧民族之蔑称了,例如——
(宋)话本《碾玉观音》:郡王(韩世忠)从墙上取下杀达子的大刀……25
(元)《老乞大新释》:况你这几个火伴的摸样,又不是汉人,又不像鞑子,不知是甚麽人。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范鳅儿双镜重圆》:其时东京一路百姓,惧怕鞑虏,都跟随车驾南渡。

进而,鉴于北方民族多食羊肉而沾染上汉人所不喜的腥膻气味,从而便有“骚达奴”这样更具贬抑性的称呼出现,例如(明)周朝俊《红梅记·城破》:
赚得些钱儿,指望拿回养家,不想这骚达奴不先不后闯将来,围了禁城,使我上不上下不下。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骚达奴”这样的语汇存在,当我们在《红楼梦》中遇到“骚达子”一词时,从字面上就很容易将其同“主食腥膻羊肉的鞑子”相联系,从而视若对蒙古民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的侮辱性称呼26。
清末民初史学家、教育家邓之诚(1887—1960)撰《骨董琐记》,引清人柴桑《京师偶记》再行转引元末明初人叶子奇(约1327—1390)《草木子》27。
元朝北人,女史必得高丽,家童必得黑厢,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贵家,必买臊鞑子小口,以多为胜,竞相夸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

若此史料不误,则表明近似“骚达奴”的“臊鞑子”一词早在元代就已出现,也颇为适应元代民族矛盾尖锐、备受欺凌的汉人和南人对处于社会阶梯金字塔顶层的蒙古人的审视心理。
显而易见,汉人这样的意识同西方人在东方主义视阈下呈现出来的妖魔化异质心态一样异曲同工,上述北师大《红楼梦》校注本所给出的相关注解,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典型反映。
无独有偶,同样浸润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译学界,在不同的日译者迻译《红楼梦》时基本上也作如是观。
松枝茂夫日译本28:蒙古人の小者(五)——五 蒙古人の小者————清朝時代,滿州貴族(八旗)の家では蒙古人の少年を召し使うことが流行し、その數の多いのを誇る風習があった。
伊藤漱平日译本29:蒙古人の小者(注八)——八 蒙古人の小者 原文「小騒達子」。「騒達子」は「臊達子」「騒韃子」とも書き、蒙古人のことをいやしめていう(清代では滿蒙人を「韃子」といい、漢人のことは「蛮子」といった)。旗人(滿州貴族)の屋敷では、この蒙古人を奴婢として用いる風があった。
具体之于这一文本细节,日译者还援引满清贵族风俗加以展开论述,这是自西方汉学借鉴而来的东洋学做派的典型表现,其言之凿凿,真有令人不得不信之架势。

早在近一个世纪前,日本学者已经在主流学界几乎全面颠覆了其传统汉学,并开辟了东洋学以及所谓支那学的新纪元,从而迅速在20世纪确立了其在中国学研究上难以撼动的国际领先地位——认真审视日本中国学的发达史,十分有助于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学术诸层面30。
日本近代东洋学的兴起,除了来自西洋东方学以及西方汉学的影响之外,更主要是西方现代学术特别是德国兰克(Leopolde von Ranke)学派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的风气影响,从而养成了注重历史原始材料科学搜集与整理的习惯,并在方法论上推重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寻找亚洲大陆诸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从而一开始就和西洋东方学差不多在同一轨道上31,这时的日本东洋学者仰仗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努力和成绩,在研究东洋学上采取俯视亚洲其他民族的立场,在认识论上都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和作为研究工具的西方学术视若他者32。
在20世纪中后期成长起来的《红楼梦》日译者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特别是后者),深谙东洋学门径,在其搜集材料的可能范围之内,为读者详尽勘订了“骚达子”的内涵和外延,充分体现出日本学界超越传统西洋东方学的模式和业绩。

从这个角度审视,日本东洋学正是今天我们追寻汉学主义“正解”在日本学界的折射——当然,东洋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非日本)国家所采取的藐视态度,则是其与汉学主义的本质区别,故而不为我们所取。
甚而至于在南欧的保加利亚译本中,即便是译者没有将“骚达子”径直译作“蒙古人”,在其接踵的脚注中却也给出了符合上述思维模式的阐释。
韩裴保加利亚译本33:вонливо варварче от Севера264——264 Северен варварин – така китайците наричали подигравателно монголите или татарите; вонлив е намек за овчите кожи, които обличали, или за овнешкото което ядели.
中文回译:来自西方的戎狄——西戎:汉人称呼蒙古人或鞑靼人;衣羊皮、食羊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保加利亚译者将“达子”视为“来自西方的戎狄”(варварче от Севера)亦即“西戎”(Северен варварин),在方位概念上出现了明显的舛误——相对于自比居于中原的正统王朝,即便是源出东北一隅的满清,其眼中的“夷狄”主要还是指来自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
从保译者的脚注看来,他是将“骚”和“达子”分开来认知的;从方法论上看,他没有援引保加利亚语中直接渊源自“鞑靼”或者“蒙古”的语汇,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杜撰出跟“西戎”意蕴切近的表达法(尽管语义有欠精准),这是消解东方主义“他者”视角、转而暗合汉学主义“己者”模式的典型表现——出自深受当代中国学术影响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保加利亚一个学者笔下,让我们看到了传统西方意识形态羁绊得以挣脱、新兴远东理论模式突围的曙光。

如果说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访学的保加利亚译者的实践,还是在最近一两年间或多或少受到由北外学者主导争议的汉学主义大讨论的话,那么,与之处理模式差可比拟的德国《红楼梦》前80回译者史华慈(Rainer Schwarz)的翻译实践,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史华慈德译文34:ein stinkiger kleiner Kamelführer“有膻味的小的骆驼牵引者”尚融
同样,德译者没有直接利用德语中固有的“鞑靼”“蒙古”等词根形成的语汇来对译,而是将“骚”和“达子”分开后,杜撰出Kamelführer“骆驼牵引者”来加以对译,这样也就自然摈弃了类似内亚族名带来的“黄祸”(英语yellow peril、德语gelbe Gefahr)色彩,以内亚游牧民族典型的关联动物——骆驼支撑起德语读者的中性想象来。
这个《红楼梦》德译本虽然正式刊行于21世纪初,但史华慈的翻译工作早在1990年就已完成。那时他还在东德,本人信仰共产主义,并有着长期的对华交往经验和工人运动研究心得。

鉴于彼时的中国尚无在理论界抗衡东方主义的底气和自觉,故而我们推想:史华慈在德译“骚达子”时的表现,与其说是其通晓中文而知华、亲华带来的下意识举动,毋宁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贯穿的各民族平等思想带给他的自觉行为——而这种翻译自觉,却又遥相呼应了20多年后我们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中大力提倡的汉学主义突破羁绊模式。
当然,还有径直将这里的“骚达子”解作“蒙古人”的译本,包括上述日译本在内。
帕纳休克俄译本35:похожей на монгола“好像蒙古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俄语中虽然有源出“鞑靼”的татарин~татарка“鞑靼族”和源出“鞑子”的таз及其复数形式тазы“达兹族”,但因其在俄语语境中容易混同于现代既有的民族,因而俄译者用“蒙古”来对译“达子”,或许可以看作一种便于俄语读者理解的变通处理。
穆旭东锡伯译本36:(

)ajige fungšun monggo“小骚蒙古人”
清代中叶从东北故地迁居新疆戍边驻防的锡伯族,本是满族的分支之一,因其聚居模式而在满语文几近消亡的今天还顽强保留了可与旧时满族相通的锡伯语言文化。
锡伯译者在将《红楼梦》译成锡伯文时把“骚达子”处理为“骚蒙古人”,明显是受了“蒙古鞑子”这一传统贬抑性表述的影响(参见东北地区旧时常见的“蒙古大夫”意指江湖游医的例子)。这个表述同西方人看待“蒙古”族名的潜意识恶感颇有相通之处。
但自13世纪用“蒙古”为统一名号的中亚游牧部落入侵欧洲、酿成至今仍令西方心有余悸的“黄祸”以来,“鞑靼”这一族名虽然时有分合,但同“蒙古”一样在西方语言中往往充满了东方主义的妖魔化异质色彩;又由于近代以降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话语权,反过来深刻影响了东方本土学者的民族思维。

《哈斯宝蒙古文版〈新译红楼梦〉》,李丽、梅花整理,远方出版社2024年8月版。
王和达捷克译本37:nějaká tatarská koketka“某种鞑靼行止”
捷克译本以其严谨、准确、精审而在捷克语乃至斯洛伐克语世界广受好评,但对于这一细节却处理得含糊其词,或许可以认为捷译者是试图以这样一种淡化处理的方式,部分抵消捷克语中源出“鞑靼”的语汇带给读者的不良感受,对照其20世纪60—80年代译竣付梓的曲折经历,不失为汉学主义未兴时突破东方主义羁绊的一种可行尝试。
李治华法译本38:petit Tartare“小鞑靼人”
赵振江西班牙译本39:una jovencita tártara“鞑靼青年”
植根于华人身份的法译者和西班牙译者将“骚达子”直接视若“鞑靼人”,刻意漏译了原文中看上去颇具贬义的“骚”字,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虽然实现了民族独立、但却从长期陷于内斗到艰难打开国内的困境反衬下,未尝不是一种尽人事、信天命而反抗东方主义之自觉意识的体现。

英语族名Tatar“欧亚草原地带(Tartary)部族及其后裔”来自古法语Tartaire,后者经由中古拉丁语Tartarus“鞑靼人、蒙古人”源出古突厥文(
英国东方学家裕尔(Henry Yule)译注《马可·波罗行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book 1, chapter 13):Persia is a great country, which was in old times very illustrious and powerful; but now the Tartars have wasted and destroyed it.——这里用的就是该族名的本义。
作为对照,下面我们仅以英语为例,对“鞑靼”对应的Tartar一词的语用情感色彩略作考察,引例不妨也就局限于《红楼梦》的英译本中。
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41:
李纨笑道:“你们听他这刁话。他领着头儿闹,引着人笑了,倒赖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儿得一个利害婆婆,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
霍克思英译42:Well,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when you marry you have a real Tartar for a mother-in-law and lots of nasty sisters-in-law with tongues as sharp as yours. It will serve you right!

第一百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43:
平儿道:“大太太住在前头,他待人刻薄,有什么信,没人送给他的。你若前门走来,就知道了;如今是后门来的,不妨事。”
杨宪益英译44:As her quarters are in the back and she's such a tartar, nobody passes on any news to her.
可见,婆婆的“利害”和大太太的“待人刻薄”,不同的贬抑情绪在不同的20世纪英译者笔下,都能诉诸同一个族名Tartar及其引申意蕴来加以活灵活现的表达,由此可见“鞑靼”族名之于西方的贬义色彩之持久了。
而如果这个族名出现在《红楼梦》英译文中,那又会呈现什么态势呢?
彭寿英译本45:a stinking Tartar“有膻味的鞑靼人”
作为第一个完整译出120回全文的《红楼梦》英译本,译者注重中文原文到英文译文之间的跨语际字面对应效果,故而“骚达子”的字面拆解在这里得到了忠实体现,长期盛行于西方的东方主义“异质”的妖魔化效果不经意间得以流露于英译文的字里行间。

杨宪益英译本46:a saucy little Tartar“粗俗的小鞑靼人”
这个英译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主推、面向西方进行外宣的正式版本,从汉语拼音业已为联合国认可、而英译全书仍然采用威妥玛拼音就可看出,该译本具有迎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倾向。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译者还是坚持了本位主义的文化立场,大量采用杜撰的意译和仿译来二度呈现《红楼梦》的纷繁表达。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看到“骚达子”就被译作“粗俗鞑靼人”,用贬义色彩较轻而相对模糊的saucy“粗俗”一词来代替贬义色彩较重而相对具体、也更能对应“骚”字语义的stinking“腥膻”加以处理,也是“中华尚未崛起”的时代试图挣脱东方主义羁绊的一种无奈之举了。
霍克思英译本47:a Tartar groom“鞑靼马夫”
身为英国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霍克思能够毅然辞去教职,潜心英译《红楼梦》前80回,表明了他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优秀元素的挚爱;而其在迻译过程中的广采博收、详尽考证和匠心独运,更是没有辜负他本人在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燕京大学游行队伍中的激情。
这里他将“骚达子”译作“鞑靼马夫”,一如前述李治华在法译时和赵振江在西译时刻意漏译“骚”字的处理,只不过,霍克思的非华人身份使得他在东方主义依然甚嚣尘上、汉学主义尚无半点峥嵘的时代,更加凸显出其呼应后来理论突破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递价值,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现今推行“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时东方主义的可破性和汉学主义的可立性具有超越国家、民族藩篱的普适性,而不仅仅是华人圈子里的自说自唱。

上述十余种《红楼梦》的译本,绵延时段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的今天共计130来年,它们对“骚达子”的认知和跨文本转换,皆是立足于中文文本的字面传统训诂而实现的。
然而,若将“骚达子”的上述内涵置于小说《红楼梦》得以成书并传抄刊行不绝如缕的清乾隆时代,立即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是文字狱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段,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统治广大汉族的满清上层,何以对这一极为触犯忌讳的文字表述熟视无睹呢?尽管在充满民族意识的江南士大夫心中始终认为满清“非正色”的“异种”,但林黛玉笑谑中称史湘云为“小骚达子”是对异族敌视的一种潜意识流露48,这样的见解显然不适用于其历经多次文字狱的“洗礼”仍然安然无恙、并且多次传抄还毫无分歧的历史事实。
要妥善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骚达子”根本就与汉文中习焉成久的民族蔑称“骚”“达子(鞑子)”毫无干系,而且为当时的满人和汉人所熟知。

清末东北人宋小濂(1860—1926)所撰《北徼纪游》49一书述及沙俄兵制50:
俄人兵制有三:曰稍达子为步兵,曰嘎扎子为马兵,曰马大罗斯为水兵。
此“稍达子”即为俄文复数形式солдаты、出自солдат“士兵”一词的汉字音译51,故而深深浸渍于混杂了大量满语成分的汉语官话东北方言中,继而引申出了“当差的、小兵儿、小人物”甚至“老毛子(俄罗斯人)”等含义52。
清代后期曹廷杰(1850—1926)所撰《西伯利东偏纪要》亦有类似沙俄兵制记载53:
查各处俄兵俱呼沙尔达士,亦讹呼臊答子。步兵、炮兵皆系该夷种类,马兵多以改装奇勒尔、俄伦春、蒙古、回民及该国雅库斯克人。
晚清朱一新(1846—1894)所撰《京师坊巷志稿》一书,在“京城往事”篇中记有位于崇文门内东城根的“臊达子胡同”、位于内城东城大兴县署胡同以北的“臊达子营”等曾有俄罗斯人聚居的北京地名54。
此外,清代北京外城和天津也有骚达子营、骚达子坟、稍子营等地名,这些却是源出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中沙俄军队从天津进军北京途中以及在北京的驻扎地55。
显而易见,这里的“臊达子”当为前述“稍达子”“沙尔达土(臊答子)”之汉字异写形式,意指“兵卒”,“臊达子胡同”即兵卒胡同,“臊达子营”即兵营而已。
以上虽是晚清的实证材料,但满清同沙俄的交往由来已久。即便从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1688)雅克萨之战算起,到曹雪芹大略完成《红楼梦》草创(未及全面修订,贫病而亡)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期间清俄两国之间频繁互使,位于东江米巷玉河中桥西岸的清初会同馆之高丽馆在《尼布楚条约》(1689)和《恰克图条约》(1727)签订后逐渐改造为来京俄国使团及商队、以及来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居住的俄罗斯南馆56,而清朝管理蒙古、回部及西藏的最高权力机关理藩院同时负责管理俄罗斯的外交事务,大量俄文典籍在此译出庋藏57。
如果说清廷严格限制两国的民间交往,那么有关俄罗斯兵制的术语则至少早早译出并在旗人中间得以流传。
由是,出身汉军包衣家庭并曾亲近皇室的曹雪芹家族,通晓类似“稍达子”“臊答子”这样源出俄文的兵制术语并非不可能,从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雪天男装的史湘云称为“骚达子”,无非将其呼作“毛子兵卒”这样的戏谑,既切合戏台上和画像中孙行者的打扮58,又丝毫不会触犯满清文字狱禁忌——这才是《红楼梦》“骚达子”得以毫无异写流传至今的合理解释。
不过,这种最为适应时代背景的解释,还有待未来的《红楼梦》译者将其体现在其译文中,从而成为汉学主义之根本——汉学研究在新时代的精微表现。

可见,仅就《红楼梦》中的“骚达子”这样一个细节,即使历经两百年的传播,仍然处于不断求索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既有的多种异族语言迻译,也从早期明显的东方主义他者幻象逐步转向了中后期的汉学主义本位意识,其间具有华裔身份和热爱中华文化的异域学者以其谨严精审的汉学考据作风支配着这一概念在跨语际表达中的扭转,而且这种行为风范还将约束我们在将来对《红楼梦》的准确译介实践活动。
对上述《红楼梦》多语种译本的细节探讨,在“骚达子”的译介平面共时展开,虽然不能完全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的所有语言(在一篇文章的篇幅内其实页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从样本抽取和剖析的角度为我们初步揭示了立足远东固有文化底蕴、开拓崭新理论视野、诠释“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有效模式,其中对早已深入人心、但却明显过时的西方理论羁绊进行合理突破,正在成为我们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注释:
1、3方维规《“汉学”和“汉学主义”刍议》,《读书》2012年第二期,第10页、第10—11页。
2、顾明栋《“汉学主义”引发的理论之争———兼与张西平先生商榷》,《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一期,第141页。
4、5张西平《关于“汉学主义”之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二期,第21页、第22页。
6、顾明栋《“汉学主义”: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新选择》,《学术月刊》2013年第四期,第19页;顾明栋《“汉学主义”引发的理论之争———兼与张西平先生商榷》,《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一期,第139页。
7、顾明栋《“汉学主义”: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新选择》,《学术月刊》2013年第四期,第18页。
8、唐均《〈红楼梦〉译介世界地图》,《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二期,第45页。
9、41、43、(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全四册),启功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611页、第522页、第1523页。
10、Cchao, Süe-čchin: Sen o Červenom pavilóne: 2. diel, preklad: Marina Čarnogurská. Bratislava: Petrus, 2001: p. 343.
11、13、Joly, Henry Bencraft (tr.): Hung Lou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hinese Novel: Vol. II. Hong Kong: Typographia Commercial, Ltd., 1893: p. 306, p. 2.
12、姜其煌《欧美红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14、刘心贞《〈红楼梦〉方言及难解词词典》,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311页。
15、(清)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上、下),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8页。
16、(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清)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6页。
17、23、(清)曹雪芹《红楼梦校注本》,张俊、聂石樵、周纪彬注释,龚书铎、武静寰、周纪彬、聂石樵校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4页、第781页。
18、(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共四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140页。
19、(清)曹雪芹《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共八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825页。
20、(清)曹雪芹《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凡六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7页。
21、(清)曹雪芹《甲辰本红楼梦》(全四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8页。
22、(清)曹雪芹《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全三册),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第579页。
24、62、65、66、68、何新华《〈红楼梦〉骚达子词义考析》,《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四期,第208页、第214页、第215页、第214—215页、第216—217页。
25、48、蓝芝嘉《〈红楼梦〉中“骚达子”之深意》,《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二期,第116页。
26、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1页。
27、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1页。
28、曹雪芹:紅樓夢(五),松枝茂夫訳,東京:岩波書店1974年版,第267、302页。
29、曹霑:紅樓夢(中),伊藤漱平訳,東京:平凡社1969年版,第126—127、132页。
30、31、32、陈怀宇《没有过去的历史:学术史上的日本东洋学——读〈日本的东方将过去转化为历史〉》,《国际汉学》2009年第一期,第280页、第284页、第284—285页。
33、Хинов, Петко Т. (прев., 2015): Цао Сюецин: Сън в алени покои (том II). София: Издателство “Изток-Запад”: п. 359.
34、Tsau, Hsüä-tjin: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oder Die Geschichte vom Stein, Kapitel 5: Spiegel der Liebe, übersetzt von Rainer Schwarz und Martin Woesler; Herausgegeben und präsentiert von der Roten Kammer-Traumwelt. Bochum: Europäi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14: S. 851.
35、Цао, Сюэцинь: 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 В 3 т. Т. 2, перевод под В. А. Панасюка и И. В. Голубева.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адомир, 1995: п. 66.
36、(拉丁转写)Ts’oo, Siyo Cin, G’oo E: Fulgiyan Taktui Tolgin (ujuci de duici debtelin), jai debtelin, Musioidung (ubaliyambumbi). Urumci: Sinjiyang Niyalma Irgen Cubanše, 1993:第1963页。
37、Cchao Süe-čchin: Sen v červeném domě: 2. Dielo, Oldřich Král (překl.). Praha: Odeon, 1986: p. 146.
38、Li, Tche-Houa et Jacqueline Alézaïs (trs.):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Vol. 1, révisé par André d’Hormon. Paris: Gallimard, 1981: p. 1132.
39、Cao, Xueqin: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Memorias de una roca): Vol. 1; traducción de Zhao Zhengjiang y de José Antonio García Sánchez, edición revisada por Alicia Relinque Eleta. Barcelona: Galaxia Gutenberg, 2009: p. 858.
40、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42、47、Cao, Xueq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Volume 2: The Crab Flower Club,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p. 791, p. 927.
44、46、Tsao, Hsueh-chin and Kao Ngo: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ume 3, translated by 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 p. 556, p. 133.
45、Bonsall, Bramwell Seaton D. Lit. (tr.): The Red Chamber Dream, Hung Lou Meng: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Chaps. 120, manuscript, 1960s; II · p. 173.
49、李德山、刘奉文《宋小濂与〈北徼纪游〉》,《图书馆学研究》1986年第五期,第139页。
60、(清)宋小濂《北徼纪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1、吕朋林《“骚达子”释源》,《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四期,第14页。
63、(清)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沈阳(奉天):辽沈书社1934年版。
64、(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5、117、128页。
67、赵云田《清朝的理藩院》,《北京观察》2013年第五期,第72—73、75页。
双悦网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